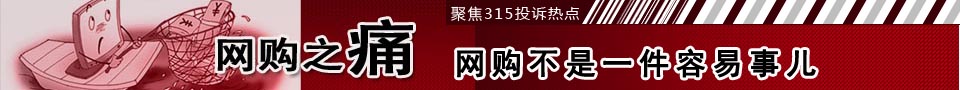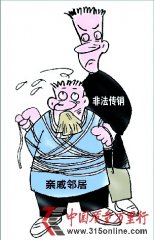繪圖:陳健珊
繪圖:陳健珊
打著商業烙印的“超適應癥”推廣,正在讓制藥企業逐漸違背美國制藥巨頭默沙東創始人喬治默克的忠告——“我們應當永遠銘記,藥物是為人類而生產,不是為追求利潤而制造的。”
7月9日,瑞士制藥巨頭羅氏瞞報8萬例死亡及不良反應案例“東窗事發”,被歐洲藥品監管部門緊急調查。一周前,美國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承認非法推廣及銷售藥物等3項指控并認罪,同意支付30億美元,創下了美國史上醫藥行業罰款之最。
兩大制藥巨頭相繼出事,讓世界醫藥第三大市場的中國為之一震。羅氏上海公司確認,涉事8款藥物中的6款在中國上市,葛蘭素史克的涉事藥物也在中國有售,但兩家藥企均稱“和中國市場無關”。
事實果真如此嗎?多位醫藥界資深人士透露,國外制藥巨頭在中國“超適應癥”用藥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國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南方日報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南方日報記者 趙兵輝 李劼
國內兩案例至今懸而未決
監管部門沒有介入導致問題藥物仍在違規使用著
這不是羅氏第一次“犯事”,2010年羅氏“安維汀”致盲事件首次將“超適應癥”用藥問題擺在中國公眾面前。
羅氏“安維汀”本是用于治療結直腸癌、非小細胞肺癌、乳腺癌、惡性膠質瘤和腎細胞癌等疾病的藥物,但是在中國它卻被用到了眼科疾病的治療中。而在“安維汀”上市之前,該藥早已在國內一些醫院暗地流通,且被醫生用于“超適應癥”治療。
上海市衛生局發布的消息稱,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對患者進行眼內注射“安維汀”藥物后,有61例患者出現眼部紅腫、視力模糊等局部反應癥狀。然而,這一明顯屬于“超適應癥”用藥的行為,最終卻被定性為“假藥門”,引發不少質疑。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姚嵐表示:“‘安維汀’的適應癥至今未做相應增加,這一行為是典型的‘超適應癥’用藥。”
繼“安維汀”之后,“拜瑞妥”在國內也被質疑“超適應癥”用藥。“拜瑞妥”化學通用名“利伐沙班”,是德國制藥巨頭拜耳醫藥保健旗下的醫生處方藥物,該藥在中國境內批準的使用說明書“適應癥”一欄顯示,“用于擇期全髖關節或膝關節置換手術成年患者,以預防靜脈血栓形成”。
今年5月,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在微博上發出質疑:“‘拜瑞妥’在歐美僅限于房顫或關節置換術的血栓預防,為何近來中國出現大量拜瑞妥用于靜脈血栓治療的情況?”由此,引發一場針對“拜瑞妥”的輿論聲討。
張強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拜瑞妥”在中國目前唯一用藥適應癥,即用于髖關節或膝關節置換手術成年患者的靜脈血栓形成的預防,根本沒有用于深靜脈血栓治療的適應癥。“但是很多深靜脈血栓患者告訴我,他們被推薦使用‘拜瑞妥’。”
對此,拜耳公司回應稱,“拜瑞妥”新的適應癥正在審批中,而這被張強認定為拜耳承認了自己是“超適應癥”推廣。
然而,令張強感到無奈的是,拜耳對此事的態度輕描淡寫,而監管部門也沒有介入,導致“拜瑞妥”依舊在被違規使用著。
利益驅動下的危險游戲
“超適應癥”推廣新藥是藥企擴大銷量的重要途徑
巨額罰款、隨時可能鬧出人命,這樣的鍘刀隨時都有可能落下,制藥巨頭們為何要鋌而走險,進行“超適應癥”推廣?
一位熟悉外企情況的人士對記者透露,利益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拜瑞妥’為例,在國內官方售價為496元,按照每天10mg的服用量計算,患者平均一天的費用接近100元。而其毛利率高達100%以上,這也就意味著病人多吃一粒拜瑞妥,中間環節就可能獲得高達55元的利益。”
有消息人士指出,拜瑞妥2011年銷售收入為1億元,其中40%來自“超適應癥”推廣:深靜脈血栓的治療。對此,張強表示,“超適應癥”用藥讓拜瑞妥的銷量翻了10-20倍。
上述熟悉情況的人士表示,“藥品管理法允許藥廠在提供足夠的臨床研究資料后增加藥物適應癥,但藥企不愿這樣做。因為藥企增加一個新的適應癥,需要進行長期的臨床研究,而這需要花費10多億美元。而一旦研發不成功,或者沒有被藥監部門審批下來,這些錢就要打水漂,所以,藥企寧愿在灰色地帶鋌而走險。”
而據張強透露,藥企申請新的適應癥,臨床試驗期一般要進行好幾年,通過藥監局審批又要好幾年。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藥企打擦邊球。“比如一種針對骨折病人血栓預防的藥,實際上根本就沒做臨床推廣,但藥企卻渾水摸魚,向骨折病人推廣。”
有醫藥行業人士分析,制藥公司之所以隱瞞不良反應的報告,大多數的原因是急于收回昂貴的新藥研制成本。因為只有推廣得越快,有越多病人使用,新藥才能夠產生更大的利潤。而對于制藥公司來說,“超適應癥”推廣新藥是借機擴大銷量的一種重要途徑。
“超適應癥”用藥普遍存在
國內目前尚無一起針對“超適應癥”用藥的處罰案例
“‘超適應癥’用藥的情況普遍存在,只要不被揪出來都不會有事。”某醫藥上市公司高層表示,國內目前尚無一起針對“超適應癥”用藥的處罰案例,這讓藥企更加肆無忌憚。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藥劑科主任吳曉松對記者表示,“在臨床上,經常會出現‘超適應癥’用藥的情況,這在國外也存在,但是因為未經臨床證實,存在醫學風險,一旦出現糾紛,醫生就要承擔責任。因此醫生往往會讓患者簽署知情書。”
據一位曾在跨國制藥企業工作過的人士介紹,外企絕對不會以公司的名義直接進行“超適應癥”推廣,而是通過學術會議或者醫藥代表個人推廣的方式,來達到“超適應癥”推廣的目的。
這一說法得到了張強的證實。據張強介紹,外企通常會舉行一些學術講座,請來講課的專家有些就是藥品代言人。
“外企進行‘超適應癥’推廣的形式很隱秘,一般披著學術的外衣,有些醫生被套進去了還不自知。這種打著學術名義的推廣,完全背離了學術本身的宗旨,給國內企業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張強表示。
雖然眾多制藥巨頭因為“超適應癥”推廣藥物被課以重罰,但是談起“超適應癥”用藥這一話題,在國內依然存在著不少爭議。
“‘超適應癥’用藥的情況普遍存在,某些藥物‘超適應癥’使用確實可以解決某類疾病。”吳曉松表示,如果某類疾病沒有可救治藥物時,醫生在臨床中一般都會嘗試“超適應癥”用藥,但前提是得到患者的同意。
姚嵐認為,安全有效的“超適應癥”用藥應當得到保護和應用,但為避免商業利益驅動下的道德滑坡,“超適應癥”用藥必須在嚴格的管理下實施。
而在張強看來,憑借一個醫生治好了一個病人的經驗,就得出所有人都可以“超適應癥”用藥的結論,這是非常草率的。張強表示,在沒有進行充分的臨床試驗前,沒有被藥監部門批準,藥品是不可以“超適應癥”使用的。
“好比開車到了十字路口,不能因為耽誤時間,就直接闖紅燈過去。等一等,對整個社會更加有益。”張強說。
相關連接
國際制藥巨頭
頻陷“超適應癥”門
翻開近年來國際制藥巨頭的“罪狀清單”,可以發現他們屢因非法營銷而被處以重罰,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藥品超適應癥”推廣。
所謂“超適應癥”推廣,是指制藥公司有意誘導超出藥品說明書適應癥范圍的用藥行為,由于超出的治療適應癥沒有經過大范圍臨床試驗驗證,存在高度用藥風險而被世界各國的法律明文禁止。通常包括兩種類型,即超出藥監部門批準的適應癥和超出批準的使用人群。
因“超適應癥”推廣,葛蘭素史克以30億美元的處罰金額占據處罰榜的榜首。未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批準,葛蘭素史克就非法銷售和推廣兩種處方藥帕羅西汀和安非他酮,并未經核準就用于治療兒童抑郁癥等疾病。它的另一項罪名是未向美國FDA報告曾經暢銷全球的糖尿病口服藥文迪雅的臨床數據。
排在榜單第二位的,是制藥老大美國輝瑞。2009年10月,輝瑞同意支付因“超適應癥”營銷而受到的23億美元的罰款,以解決對其止痛藥“伐地考昔”等四款藥物銷售欺詐的指控和相關刑事以及民事責任。
世界最大跨國制藥企業之一的瑞士羅氏公司,此次因瞞報1.5萬份使用該公司藥品患者死亡的不良反應報告,以及沒有評估由患者記錄的約6.5萬份藥品副作用報告,或將成為下一個被重罰的制藥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