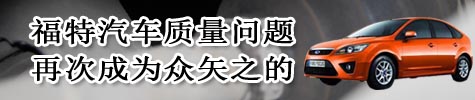新金融記者 陳一昀 張沙莎西安報道
糾紛
對于王耀輝而言,今年的“3·15”,或許又不平靜。確切說,自從2011年開始,每年的這一天就成為了王耀輝最為積極的一天。
“我在3·15鬧過事,3·15可以投訴,我去投訴。”王耀輝從不否認,作為西安一位普通消費者,其這兩年四處“鬧”——發過傳單、簽過橫幅、找過媒體、到處投訴。而目的只有一個,狀告“假北京同仁堂非法行醫”。
盡管已是陳年往事,但王耀輝至今仍能娓娓道來昔日的每一個細節。
2009年9月,王耀輝曾兩次到位于西安高新區團結南路上一家掛著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藥店就診,坐診大夫為田永成。田永成先后為王耀輝開了兩個處方,第一個處方中包含紅參須12g、黃芪30g等約20種藥材,主治濕氣。王耀輝在服用三天未見好轉、身體反感不適的情況下再度問診,田永成進而為其開出了第二個處方,這次的處方中并不包含紅參須,藥材種類減少為12種。
然而在按照第二個處方連續服用兩天后,王耀輝的不適感更加明顯了。“血壓升高、心率變快、晚上十點鐘我就開始渾身冒熱汗,心臟燥得很。”似乎一時間王耀輝身體的各種“毛病”全都爆發出來。
此后的日子里,王耀輝開始常年在西安市中醫醫院就診,通過服用中藥、針灸治療與中醫按摩來恢復身體。據王耀輝回憶,嚴重的時候,“光頭上的針就有30個左右,現在扎的話,頭上可能10個左右。”
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田永成首當其沖。事后,王耀輝曾多次到這家掛著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藥店“討要”說法。也正是在此過程中,王耀輝被該藥店一位段姓大夫告知,田永成所開的第一個處方里的紅參須在秋季過量了,第二個處方則沒有問題。
此后,王耀輝一度拿著兩個處方到處請人查看,并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文字呈現在博客上。其得到的回應中,關于紅參須過量的說法比比皆是,但愿意幫她為此說法開具書面證明的醫師卻寥寥無幾。
想象得到的,事情接下來的發展同其他任何一樁普通醫療糾紛無異——投訴、上訪、提起訴訟;想象不到的,這并非一場循規蹈矩的醫療糾紛——坐診醫師沒有行醫資格、掛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藥店變成了“冒牌貨”。
資質
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2011年。王耀輝依稀記得,那一年的“3·15”之后其選擇到誤診藥店門口發傳單,以此來控訴自己的不幸遭遇。至此之后,其陸續接到匿名電話,其中有消息指出,田永成原是微波廠(現已更名)職工,且無執業醫師資質。
為了確保匿名電話所述內容的真實性,王耀輝曾到微波廠、微波廠家屬樓即田永成住處詢問。近日,新金融記者與王耀輝一同再次來到微波廠了解情況。雖然該廠勞資科人員表示不予提供田永成檔案,但并未否認田永成曾在該廠工作。
由于田永成早已將房屋出租,搬離微波廠家屬樓,并未見到其人,但通過向其鄰居及小區內曾在微波廠工作過的其他職工了解,不難得知,“他在廠里早早就下崗了”,“他在單位時不看病”,“現在不知道他在哪個藥店坐診”。
隨后,新金融記者來到王耀輝被誤診的藥店暗訪,在該藥店坐診近七年的坐診醫師趙茹鳳告訴新金融記者,田永成早就不在這家藥店了。
而在談到田永成的醫術時,趙茹鳳則表示:“他(看病)看得咋樣不咋樣(不好說),反正中間有一位病人來鬧他的事,那個病人到處告、到處鬧,老田本身就不是正牌醫生,他沒有執業醫師證,她就抓住他這一點,鬧得沒完。”
正如趙茹鳳所言,新金融記者通過衛生部網站執業醫師信息查詢,陜西省內,并沒有查詢到與田永成相關的信息。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該信息查詢處、陜西省一欄中,也并未能查詢到與趙茹鳳相關的內容。按照其提供名片上的“趙茹風”三個字進行查詢,也無結果。
當然,不排除上述兩位醫師所注冊的執業醫師資格是在陜西省以外地區,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經注冊后,可以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按照注冊的執業地點、職業類別、執業范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健業務;醫師變更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范圍等注冊事項的,應當到準予注冊的衛生行政部門依照規定辦理變更注冊手續。
這意味著,至少,這家掛著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藥店,對于自己店內聘請的坐診醫師的管理或多或少存在著漏洞。
而相較王耀輝日后發現的事情,這也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欺騙
在王耀輝的投訴名單中,自然少不了北京同仁堂。
王耀輝告訴新金融記者,其曾通過北京同仁堂官網公布的電話號碼進行投訴,第二天便收到回應——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藥房(下稱西大街店)國醫館趙館長和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藥房科技路店(下稱科技路店)許店長找到王耀輝了解情況。
而正是這次溝通,王耀輝方才知道自己去了一家“假同仁堂”藥店——這家藥店店內外的裝潢風格與其他北京同仁堂藥店幾乎一致,店內隨處可見“北京同仁堂”或“北京同仁堂健康藥業”字眼,就連貨架上所陳列的商品也多半與北京同仁堂有關,不僅如此,店內所設的兩間中醫診室也與其他北京同仁堂的如出一轍。即便如此,它卻切切實實不是北京同仁堂藥店。
已經由西大街店國醫館館長調任為科技路店店長的趙店長向新金融記者表示:“(王耀輝)談的時候我們也是一頭霧水,最后我們明白了,原來是豐慶堂那邊的事情。”趙店長口中的豐慶堂,才是王耀輝所就診藥店的真實面目。新金融記者從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拿到的工商資料顯示,該藥店的實際注冊名稱為西安豐慶堂大藥房有限公司(下稱豐慶堂),于2007年5月注冊成立,有兩位自然人股東,其中柳銀輝控股80%,王小燕持股20%。
事實上,豐慶堂與北京同仁堂并非全無關系。新金融記者走訪豐慶堂時發現,柜臺上放著名為“北京同仁堂健康會員手冊”的小冊子,冊子內“大型專賣店”列表中并未提及豐慶堂,不過在“大型專柜”中,確有“西安豐慶堂專柜”一說,地址也正是豐慶堂所在。店內員工有些不耐煩地解釋說,“這是豐慶堂藥房,不是北京同仁堂的,我們這兒設的是專柜。”
這意味著,豐慶堂可以賣北京同仁堂的藥品,但其與北京同仁堂的關系,也僅此而已。其既不是北京同仁堂藥店,不能用北京同仁堂的招牌,也不該使用印有“北京同仁堂”的處方。
在西安市雁塔區衛生局于2011年11月出示的一份處理情況匯報中表示,藥房(指豐慶堂)經北京同仁堂授權,可開設專柜銷售北京同仁堂藥品,藥房整體裝修風格參照同仁堂,診所設在藥房內部,存在執業機構名稱標示不明顯問題,同時在現場檢查時發現少量印有“北京同仁堂”的處方。對此,已進行了處罰,責令其停業整頓,目前已整改到位,重新開業。
在趙店長的印象中,豐慶堂前后換過幾次招牌。最早的時候它直接掛的是“北京同仁堂專營”幾個字,后來一段時間變為“北京同仁堂阿膠熬制站”,現在掛著的招牌是“北京同仁堂參茸西安站”。
有趣的是,幾個招牌中,雖然“北京同仁堂”五個字的字體與后面幾個字是區分開的,但這五個字始終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新金融記者并未在店內看到與“北京同仁堂”同樣醒目的“豐慶堂”的大字招牌。
對此,豐慶堂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東柳銀輝的哥哥柳銀平只是回應說,“一進門玻璃上貼著張東西,包括公示,那么大一個工商局制的東西,統一制的一個公示,起碼有一平方米吧。”并沒有明確回答豐慶堂大招牌掛在哪里的疑問。與此同時,雖然豐慶堂處方箋上已無“北京同仁堂”字樣,但掛號單上方至今仍標有“北京同仁堂國醫館”字樣。
坦白而言,北京同仁堂的招牌為這里增添了不少客流量。2月27日下午5點,前來就診、拿藥的人絡繹不絕,在兩間中醫診室門外,更是等候著十余位已經掛號的人。在這些人看來,這家充斥著北京同仁堂氣息的藥店正是北京同仁堂藥店,他們也因此而來。
殃及
不得不說,豐慶堂的違規殃及了北京同仁堂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
在陜西省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查到的工商資料顯示,北京同仁堂陜西藥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陜西藥業)除北京同仁堂商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方控股65%之外,還有一位自然人股東——柳銀輝,持股35%。同時,柳銀平與王小燕在陜西藥業擔任董事。
如上所述,柳銀輝、王小燕則正是豐慶堂的股東。對于“雙重身份”,柳銀輝表示他并不參與陜西藥業的經營,柳銀平也表示這只是柳銀輝的個人投資行為。一位在陜西藥業工作快十年,與其總經理同一間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向新金融記者表示,他個人認識柳銀輝,但柳銀輝“跟單位沒任何關系”。
即便如此,作為受害者的王耀輝仍認為自己的遭遇北京同仁堂難辭其咎。其始終認為,豐慶堂店外“北京同仁堂”幾個大字招牌如此醒目,卻“沒人管,當時我也是很震驚。”
在王耀輝同北京同仁堂的“戰爭”中,一方認為北京同仁堂接到投訴后僅表明不關自己事、沒有進一步表示的“不了了之”的態度大有縱容之嫌;一方則以將情況逐級匯報、派人調查、關注對方是否換招牌決定是否再匯報等舉措表明了在此事件上的仁至義盡。
其實,整個事情并不復雜:消費者在一個盜用百年老店招牌的店里,撞上了一個沒有執業醫師資格的坐診醫師,被誤診,并在日后的協調中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這本就是一場普通的醫療糾紛,原本的孰是孰非很明顯,原本的責任歸屬很清晰,但就是硬生生地在各自算盤的盤算下,事情紛繁復雜,懸而未決。
不得不說,多年拉扯下來,各方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消費者身體本就受到創傷,如今還要經受心理折磨;豐慶堂已為自己的行為埋單過一次,如今還要時時接受來自北京同仁堂及社會輿論的監督;北京同仁堂一方面被冒充,一方面被質疑,也算得上“躺著中槍”。
而事實上,監管機構、法律法規又有哪一個躲過了“王耀輝事件”的這顆子彈呢。
多年來,無論是中醫企業尷尬、中醫醫院尷尬、中醫藥店尷尬、中醫教育尷尬、中醫立法尷尬,無論是哪個尷尬,都是中國中醫藥行業的尷尬,都是中國中醫藥行業之痛。
早在2004年北京香山會議宣讀的“中醫藥戰略地位研究報告”一文中曾指出:“面對中醫在西方世界的興旺,我們完全有理由擔心,也許未來中國要到西方去取中醫藥的真經。”因而,從某種程度而言,反思“王耀輝事件”,并真正解決“王耀輝事件”所折射出的問題,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