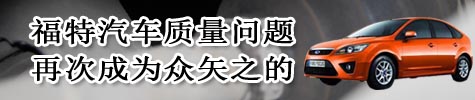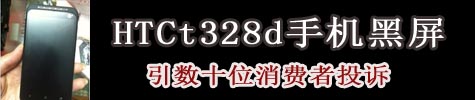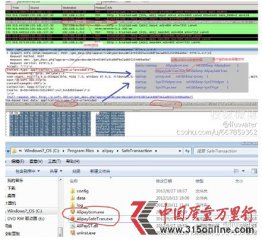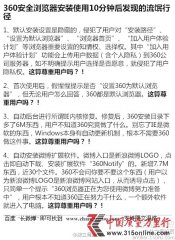然而,這些文件大多是針對具體問題,在總體上,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法律法規,卻仍然不成體系,對基礎網絡建設信息安全領域保護,更是缺少明確的、體系化的法律文本。
《財經國家周刊》從工業和信息化部(下稱“工信部”)相關部門獲得的資料表明,工信部2011年已經啟動信息保護立法調研和研究工作,并約談了包括百度、騰訊等諸多互聯網公司。
監管調整
降了立法層面之外,專家也建議,中國應建立更加立體化的國家網絡信息安全評估保障機制。
一位資深行業人士說,中國一直沒有真正著手信息安全體系,更多是由于歷史原因。
“就最基礎的通信設備和網絡設備來說,中國最早是沒有自己的工業基礎的,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依賴進口,而且在早期我們還處于大發展階段,每年都需要興建大量的網絡,在那個階段,對系統設備的要求基本上只有最低的要求:能用就行。”該人士說,雖然當年的信產部及后來的工信部,都設立了入網檢測機構與檢測程序,但這一程序也更多是對于設備可用性的檢測,對信息安全的評估并沒有提到最為重要的等級。
但隨著時代變化,當各國的信息通信流量爆漲,并全面滲透進入政府、軍事、商業、工業與公眾服務的各個環節之后,信息安全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
“信息安全關系到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國防安全和社會穩定,尤其網絡信息安全已經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的第一安全,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也就直接關系對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能力。”工信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主任邱善勤說,當前,世界各國都將信息技術和信息安全的自主可控能力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緊密聯系在一起,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甚至已經對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經貿等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
與此同時,信息安全事故的破壞性越來越大,信息安全問題也越來越成為焦點。近兩年來,微軟、亞馬遜、谷歌等企業紛紛發生重大信息安全事故,“震網”病毒更給伊朗造成巨大損失。信息安全事故頻發,也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比如在美國,奧巴馬將網絡安全問題視為最嚴重的國家經濟和國家安全挑戰之一,提出將數字基礎設施視為國家戰略資產予以保護,并組建了網絡戰司令部。日本則通過了《保護國民信息安全戰略》,重點加強鐵路、金融系統重要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防范。
“這也是為什么利益相關方以信息安全為借口指控中興華為時,美國各方立刻高度緊張的原因。”前文提及資深行業人士說。
問題在于,由于過去在開放環境下的高速發展,中國過去是既沒有行業標準,也沒有法律要求,沒有合格的檢測機構,對于信息安全成體系的評估監管,尤其在設備領域,幾乎是一個空白。該人士說,在此過程中,過去政府對行業基本沒有做強制性的規范,也缺乏強制手段和檢測手段,而是把權放給了基礎運營商,但在商業環境下,運營商所進行的檢測乃至防范往往會不自覺地放松要求。
“所以,中國現在除了繼續開放市場,積極與海外廠商合作外,也要注意保護與捍衛自己的核心利益與國家安全,重新改變政府與企業過去在對信息安全體系中的定位和分工。”陳金橋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