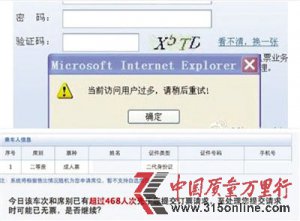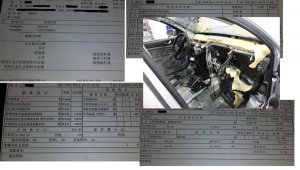日前,我國《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通過,巧的是就在同一天,豐田汽車宣布在全球范圍內召回743萬輛汽車,其中在國內預計召回139萬輛,創下中國汽車市場的最大召回規模。
在苦等十年后,中國《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條例(草案)》終于得以通過,并從規章制度上升為法規,這也意味著“千萬級罰金”今后將對明知有缺陷拒不召回的企業產生巨大震懾作用。無疑,汽車產品召回相關管理法律層級的提高,會讓更多的汽車消費者受到充分的保護。 據了解,按照條例規定,若按處缺陷汽車產品貨值金額10%罰款的最高額度,即便是對于均價10萬元的自主品牌乘用車,按照同一批次1000輛的保守估計數,企業也將面臨“千萬級罰金”,隨著上述條例得以“落地”,預計未來在華銷售的進口車、合資車和自主車將在召回頻次、召回批次、單批次召回量等方面大幅增加。相對于自2004年實施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簡稱“管理規定”),條例新增規定,生產者或經營者出現“未停止生產、銷售或者進口缺陷汽車產品的”“生產者經責令召回拒不召回的”,將被處缺陷汽車產品貨值金額2%以上10%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并處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由許可機關吊銷有關許可。
我們的汽車銷量世界第一,但是質量管理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在汽車生產大國里倒數第一。根據質檢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的數據,2009年美國新車銷售1043萬輛,召回1784萬輛,571次,相當于銷量的170%;日本新車銷售460萬輛,召回311萬輛,291次;中國新車銷售1364萬輛,居全球第一,召回136萬輛,56次,僅為銷量的1/10。比起汽車消費市場大踏步向前的發展速度,我國的汽車召回政策明顯滯后了。
正是這樣的背景使得人們對《條例》的問世充滿期待。
汽車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此前實施的《缺陷汽車召回管理規定》中,對于“企圖隱瞞缺陷的汽車制造商”的懲處辦法是:“除必須重新召回、通報批評外,還將處以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這樣的處罰力度,對于汽車企業顯然沒有任何“震懾力”。比起老“規定”,《條例》的皮鞭顯得兇悍了不少。一旦涉及車輛數目上萬輛,罰金甚至可能過億,這種嚴厲的處罰力度將對車企產生一定的震懾作用,明知有缺陷卻拒不召回,或者召回后拒不消除缺陷的行為或將因此減少。
自主品牌車召回不到一成
近年來,隨著召回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涉及品牌越來越廣,人們對于召回的認識,逐漸從最初的不解變成如今的理性。車主們不再把召回看得如洪水猛獸一般,而是更愿意把召回看成是車企的一種負責任的體現。因此如今的召回,未必會損傷品牌形象,反而更有可能博得市場好感。
中國消費者對于召回的態度在進步,但是中國汽車品牌對于召回,卻還處在令人“怒其不爭”的狀態。據統計,2010年,我國汽車召回案例為95起,本土品牌的案例僅為2起。2011年,我國汽車召回案例為71起,而本土品牌的案例也僅為2起。
記者查詢國家質檢總局官網發現,2012年上半年,從1月11日第一起汽車召回事件算起,截至6月底,共發生31起汽車召回事件,涉及車輛約102余萬輛。其中,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共發生四次汽車召回事件,涉及車輛52.8萬,兩項指標都占據第一。
根據國家質檢總局官網公布的召回情況統計,2012年1~6月共有31起汽車召回事件,2起為國產自主品牌汽車,18起為外資品牌,11起為合資品牌,國產汽車占到總數約6%。與國產汽車的低召回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系車召回率較高。
今年上半年,共有6家車企發生了兩次以上的汽車召回事件:分別為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法拉利瑪莎拉蒂汽車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本田技研工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寶馬(中國)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以及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等。
其中,日產與本田均發生了兩次召回,東風本田為4次召回,涉及車型包括2004款思威(CR-V)牌多用途乘用車、思威(CR-V)牌多用途乘用車以及思域(CIVIC)牌轎車,排在“召回次數排行榜”第一位。
對此現象,資深汽車經理人浙江米卡迪總經理張建業認為,《條例》的頒布,對于之前在召回方面存在短板的自主品牌,將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無論是車子本身的設計問題,還是車子零部件的問題,將來自主品牌再想逃避召回,將要面臨的可能就是巨大的違法成本。
確保汽車召回制實施,配套措施需跟進
汽車召回條例升級,車主權益受到了更好的保護。然而,有法可依,并不意味著執法必嚴。
就缺陷汽車產品召回條例的實際內容來看,沒有一個專業的監管機構和健全的專業維權隊伍,每一個消費者仍然具有實施投訴的難度。因為就一個汽車產品所存在的缺陷來看,其涉及到的經濟金額很小,消費者就很難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實施維權行為,大部分消費者或許只有選擇長期、耐心地等待遙遙無期的結果。
目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的召回案例,都以被動召回居多。也就是說,通常都是通過監管部門檢驗出汽車產品存在質量問題,再責令車企進行召回。在歐美和日本,這種監管機制已經比較成熟,因此有不少召回案例都是由國家發起。
而如今的《條例》,對于監管權責的劃分、檢測機構的配備、相關配套政策法規的完善都無法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缺少這些角色,光靠《條例》唱獨角戲,這出戲的可看程度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