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借著移動互聯網和社交網絡的東風,微商的概念迅速崛起,并且發展出多種新型的商業模式,向傳統電子商務發起了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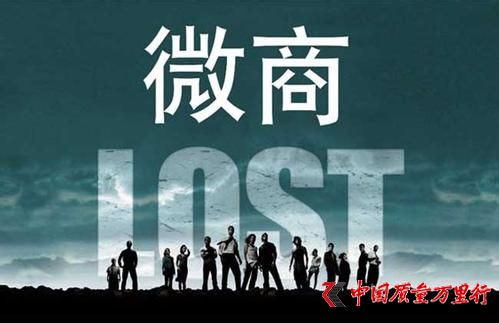
據中國互聯網協會微商工作組統計,2015年我國微商從業人員就已超過1200萬人。在經濟以傳統制造業為主向新興服務業為主的換擋過程中,微商一方面為就業弱勢群體提供了一項選擇,另一方面也幫助企業降低了產品流通的成本。
不過,微商在發展中也遇到了不容忽視的挑戰,部分微商銷售的產品在質量水平、售后服務上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現一些故意坑害消費者的“黑微商”。此外,有的微商商城為牟取暴利,利用層級網絡不斷發展下線,開展非法傳銷活動。
有專家估計,目前國內4000多萬微商中,相當部分已經發展成為傳銷。專家認為,微商與傳銷的重要區別在于產品是否最終被消費、是否為實體經濟服務。并且,微商也是“商”,不是法外之地,也應該納入監管。應防范以微商之名,行傳銷之實,對社會造成危害的現象。
微商行業野蠻生長
今年22歲的女大學生萌萌(化名),從大二起就開始在朋友圈銷售面膜。由于她推銷的保濕面膜售價較低,適合學生的消費水平,一些周圍同學都成為萌萌的長期客戶。到大三時她的月收入已經達到十幾萬元。
不需要有實體店也不需要工商注冊,萌萌就能做起自己的小生意,她定期從上家拿貨,需要全款支付,囤積在宿舍里。此外,她還要接受培訓,學習如何利用社交網絡推銷產品。
萌萌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跟客戶交流上。她在QQ空間、微信朋友圈中發布商品信息,交流產品使用的心得,獲得買家的信任。短時間里,她對商業談判、市場營銷、庫存管理都有了親身實踐,結識許多朋友,在她看來,“微商圈的人都特別勵志”。
萌萌也會遇到有上家把貨甩給她后就失聯的情況,這些商品往往是賣不出去的劣質產品,這時候萌萌只有自認倒霉,以后多加留心。她把倒霉的事分享給同是微商的好友們,讓大家都提防這家“黑微商”。
有時,萌萌還需要在朋友圈“炫富”,吸引其他人加入微商行列。如果她能發展自己的“下線”,那么就能賣出更多貨,同時以更低的成本從上家拿貨,這比直接面向消費者賺錢更容易。不過,萌萌更喜歡做零售,這能讓她更貼近消費市場,更充分地和“粉絲”們互動。
曾有線下實體店經營經驗的小林(化名)也發現微商比實體店機會更好。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微商事業,每天進貨、拓展客戶群體,參加培訓提高銷售技巧。由于業績優異,他還有機會參加微商品牌內部組織的晚會和出游活動。
雖然小林代理的并非知名品牌,但由于有實體經營背景,他能拿到國際大牌代工廠生產的產品,因此和其他微商品牌相比,他推銷的產品質量較高,在微商市場上有一定競爭力,客戶復購率也很高。
小林告訴記者:“從事微商最難的是建立起信任感,要讓別人對自己從不信任到信任,再到購買產品,最后成為你的下線并且開展自己的銷售渠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按照中國互聯網協會微商工作組2015年的統計數據,和小林、萌萌一樣從事微商行業的人數已達到1257萬人。
盡管微商發展勢頭迅猛,也為許多人創造了財富。然而,與生俱來的草根特質,加上監管缺位下的野蠻生長,微商的成長腳步始終伴隨著質疑之聲。從最初的九宮格照片刷屏,到如今的雞湯、廣告泛濫,微商還沒有成為多數公眾認可的主流商業模式。
和傳統電商不同,微商是通過在社交網絡上分享個人的消費體驗,一傳十、十傳百,引起關注后形成購買力。所以微商營銷既依賴于口碑,也依賴于網狀層級結構。隨著朋友圈賣貨信息的逐漸增多,微商的體驗開始變差,部分微商開始透支商業信譽和社交資源,用戶黏性變差。
網友小楠(化名)告訴記者,微商最讓她反感的還不是商品質量不好,而是很多微商好友“暴力刷屏”。當她刷新朋友圈想看好友動態時,總會撲面而來滿屏幕的賣貨信息。在她看來,社交商業是基于推薦者非常了解一款商品,如果自己不懂商品,什么賺錢就推銷什么,就有違微商的初衷。
由于缺乏統一的規范和監管,微商一直存在假冒偽劣商品頻現、售后責任難以追究、資金欺詐等亂象。還有一些不法分子打著微商的旗號,從事傳銷活動,危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2016年4月~6月期間,一個名為“萬事有我”的微信公眾號在韶關市、廣州市兩地利用手機微信傳播推廣,并利用公眾號內的“無上商城”購物返利和發展下線消費拿提成和傭金的方式進行傳銷活動,已發展層級三層以上,參與人數超過8000人,非法實際盈利31萬余元。目前該公眾號已經關閉,很多參與者投入的資金血本無歸。
去年9月,合肥警方查獲一個以電商平臺為幌子的傳銷窩點“云夢生活”,刑事拘留27人、行政處罰34人。
警方發現“云夢生活”實施拉人頭、交納入門費等多種形式傳銷活動。警方提取的后臺數據顯示,該傳銷組織已發展注冊會員多達28萬余人,層級達214層,交納會費人員達3萬余人,涉案金額高達2.8億元。
微商平臺頻繁涉嫌傳銷
微商最早誕生于2012年初,隨著微博、微信先后擁有巨量用戶,朋友圈、微信支付、公眾號等功能推出,沒有商業經驗的個人就能輕松完成從產品批發、產品推介到資金收付、發貨、用戶反饋的整個銷售鏈條。
2014年,一大批品牌微商先后成立,專業化的微商平臺也應運而生,微商從單打獨斗進入團隊化運作時期。
某微店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由于科技進步帶來生產效率提升,一些傳統就業崗位萎縮,剩余勞動力便涌入微商行業。尤其是在就業市場受到歧視的弱勢群體、空閑時間較多的大學生等,已經成為從事微商的主要人群。
他認為,和淘寶、京東等傳統電商平臺不同,微商不需要長時間的信任積累和習慣培養,天然就是熟人之間的商業環境,更容易建立起信任,這是大量微商代購興起的原因。
同時,隨著傳統電商流量紅利的逐漸減少,移動與社交相結合的微商市場成為各電商及品牌競相布局的渠道之一。今年5月,艾瑞咨詢發布《2017年中國微商行業研究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微商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3200多億元,預計2018年將達到7000多億元。
2016年中國互聯網協會微商工作組發布《2016中國微商行業發展研究報告》,將微商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基于人際關系網絡,利用互聯網移動社交工具從事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
雖然微商能享受到社交平臺帶來的流量、信任度、傳播方面的各種便利,但也正因為根植于社交網絡,微商一旦出現不誠信事件就會導致個人社會關系的惡化。而呈組織化、團隊運作的微商一旦出現惡性事件,將對社會公眾造成不可忽視的危害。
實際上,大部分微商都采取組織化和層級運營模式。小林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微商內部存在董事、總代理、一級代理、二級代理四個級別,每個董事管理100個總代,低級別代理從高一級代理拿貨,級別越高價格越低,毛利也就越高,并且都比零售價便宜至少一半。
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一份某微商內部晉升機制方案顯示,該微商存在“經理-主管-店主”三層,繳納最低398元平臺服務費就能成為普通店主,店主可以將產品銷售鏈接轉發到朋友圈,只要有人購買就能抽成10%至40%的傭金。
如果店主業績好、下線發展得快,可以升級為主管,領導自己的店主團隊以后,可以從每一名新店主身上提取150元培訓費,分得團隊利潤的15%。在競聘成經理后,可以獲得下轄所有團隊店主培訓費每人80元,以及各團隊總利潤的5%。與店主不同,主管、經理需與微商簽訂兼職勞動合同,該微商后兩者的數量就達七八千人。
除了層層代理賺取差價,培訓更是團隊化微商的中心環節,新加入店主將學習吸引他人的技巧,如何推出成功案例、設計心靈雞湯等。
以上的模式在微商中比較普遍,也引起了是否傳銷的爭議。根據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禁止傳銷條例》,傳銷行為的三個主要特點是: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
2013年1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指出,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
2016年3月,國家工商總局公布《新型傳銷活動風險預警提示》指出,不管傳銷組織如何變換手法偽裝自己,只要同時具備“交入門費”“拉人頭”“組成層級團隊計酬”就可認定為涉嫌傳銷。
今年8月,“云集微店”、“環球捕手”和“7mall”等多家社交電商平臺的微信公眾號被封,騰訊對“環球捕手”給出的封禁理由是“此賬號存在涉嫌多級分銷經營違規行為”,并且已清退該賬號綁定的微信支付商戶號。記者同時了解到,云集微店5月就被浙江工商定性為傳銷,處罰沒款958萬元。
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唐春林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微商平臺的人員計酬和返點是以邀請加入的人員數量為基礎,就符合傳銷的本質特征。”
目前,雖然警方已經破獲了“萬事有我”、“云夢生活”等傳銷類微商平臺,但是如何防范微商異化為傳銷還有待相關規則更加明確和監管就位。
微商也是商,監管要跟上
2016年7月,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武長海發布了中國首份微傳銷研究報告,將近幾年來傳銷組織開始利用智能手機,通過微信群、微信公眾號、手機QQ群、QQ語音聊天室、陌陌等社交平臺進行傳銷的行為定義為“微傳銷”。
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國內微商有4000多萬家,如果嚴格按照傳銷定義,其中相當部分已經發展成傳銷。他認為,微商是否涉嫌傳銷,除了通過是否同時具備傳銷的三個特征來判定,還可重點看其產品是最終消費了,還是僅僅作為參與者獲利的一種傳遞媒介。
武長海指出,涉嫌傳銷的微商不是靠產品最終銷售利潤來維持,而是后進入者的本金。通常上級會員會讓下級會員買大量產品,造成產品積壓,最終消費部分很少,淪為沒有形成利潤的無效交易。
北京昊漢律師事務所律師曹晉義指出,傳銷活動為了吸引下線參與傳銷網絡,只能不斷抬高商品價格。這違反市場經濟規律,注定難以為繼,最終要么關門,要么演變為龐氏騙局。
“如果微商平臺不將平臺價值體現在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上,不回歸以追求真實銷售的擴大為商業目標,恐其社會危害性將不斷擴大,最終將一個打著新興商業模式旗號的創業活動,演變成違法犯罪的傳銷活動。”唐春林表示。
有業內人士同時指出,一些平臺型微商即使產品進入最終消費,但類傳銷的激勵機制也存在風險。給予店主層級返利有違口碑營銷的初衷,其好友可能并不知道店主能夠從中抽成,而店主對產品的評價未必客觀真實。
他認為,通過分享商品鏈接讓好友消費并從中抽點,本質上更類似于付費刷單電商模式中的有償評價和虛假買單,而不是真正意義的社交電商。
武長海還認為,微商也是商人,經商就要有資質,應有準入門檻。凡是商業經營活動就要納入監管視野,不能為所欲為,要接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食品藥品安全法等法律規制。
他表示,《禁止傳銷條例》與現在的傳銷發展相比已遠遠落后,對于傳銷的監管部門目前主要依靠工商部門,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需要各部門配合性執法、聯合執法。
他建議,可以由網信辦、工信部、工商總局等多部門聯合制定管理辦法,將微商納入監管,至少實行簡單備案制,尤其對資金去向進行監管。此外,支付寶、微信、QQ等相關平臺企業也要履行社會責任,進行技術研發主動監管,及早發現問題,控制風險。
2015年11月,工商總局發布《關于加強網絡市場監管的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將微商納入監管范圍,要求研究規范微信等社交網絡營銷行為,研究社交電商等新型業態的發展變化,有針對性地提出監管的措施辦法等。
去年3月,工商總局公布《新型傳銷活動風險預警提示》,就一些傳銷組織采用所謂“微商”“電商”“多層分銷”“消費投資”“旅游互助”等名義,以高額回報為誘餌,發展人員形成上下線關系,推銷產品和服務,從事傳銷活動,向廣大群眾進行預警提示。
今年1月,中國電子商會微商專委會等發布《微商行業規范》征求意見稿,指出微商服務者應當依法辦理工商登記,并履行必要的行政許可或備案程序。微商服務者為企業的,應向微信等互聯網第三方平臺提供企業名稱、營業執照副本照片、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姓名、有效手機號碼、對公銀行賬號等信息;微商服務者為個人的,應向第三方平臺提供真實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銀行卡號等信息。微商經營者交易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兩年。
征求意見稿提出,微商活動禁止任何形式的傳銷。微商傳銷是指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