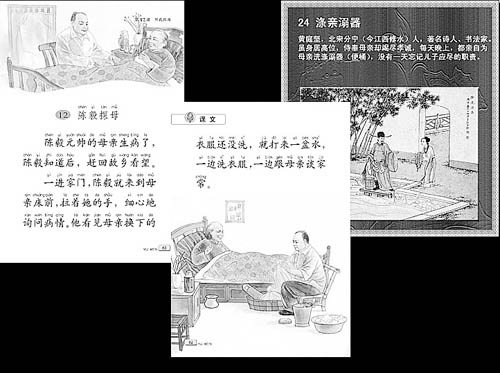
10月12日、13日,作家葉開在其個人博客上發表日志,以其女兒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鳥的天堂》和《一顆小豌豆》為例,比對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寫后的小學語文課文之間的差別。而此前,今年9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也將矛頭對準了小學語文教材。
該書以教材點評的方式,刊發了一個名為“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民間研究團體的研究報告——他們以目前使用最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學語文教材(以下分別簡稱“人教版”教材、“蘇教版”教材和“北師大版”教材)中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為研究對象,認為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3版本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為“-2分”、“-1分”和“0分”
2008年,一直為《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撰寫專欄的語文教師郭初陽發現,目前小學語文教材選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親形象和反映的母愛是“病態”的。
“郭初陽提出看法后,我們馬上查驗文本,確實發現存在太多問題。”《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執行主編李玉龍有了組織團隊進行系統專項研究的想法。李玉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出面于2008年10月18日在浙江蕭山召集一些核心成員開會,牽頭成立了“母親·母愛”研究課題組。
如今被浙江媒體稱為“麻辣教師”的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在課題組中被委以學術主持人的重任,負責“人教版”教材中相關文本點評的統籌。“蘇教版”教材的統籌和“北師大版”教材的統籌工作分別由郭初陽和呂棟擔當,最后由李玉龍統稿。
經討論,研究團隊將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母親”、“母”(意為母親)、“媽媽”、“媽”、“娘”的課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親只是主體情節的點綴或僅起到穿針引線結構功能”的課文,從“人教版”、“蘇教版”和“北師大版”中分別精選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課文、選讀課文、略讀課文和習作)涉及母親與母愛的文章進行打分和點評。
打分的判斷原則是:是否符合公民社會價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實、是否有切實性。記者看到,在入選點評范圍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獲得了5分的評價,接近半數(33篇)文章的得分為負數。3個版本的教材所選文章的總得分分別是“-2分”、“-1分”和“0分”。
在總評中,蔡朝陽指出了上述3個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別是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
他舉例說:“原來瑯瑯上口的《游子吟》,被費盡心思地包裝起來,仿佛農民家里新買了空調,室內機上頗費氣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為是偉大的發明,其實臃腫而贅余”。
課題組還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對一些文本的事實進行考證。例如,他們對課文《愛迪生救媽媽》的真實性進行了求證,委托在美國留學的學生查文獻、向醫學專家求證,得出的結論是:“最早的急性闌尾炎手術是出現19世紀末,最早對闌尾炎手術的論述是1886年。愛迪生生于1847年,電燈發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經是一個40歲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說,愛迪生小時候根本沒有闌尾炎手術,不可能有一個醫生在他做的有影燈下為他得了急性闌尾炎的媽媽做了這個緊急手術——這個故事是虛構的。”
質疑權威是為了孩子
2009年年初,研究團隊形成了一份20萬余字的課題報告,《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刊發了其大部分內容。此后,課題組還將該報告的全文發布到網上。
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國內媒體刊發了對這項研究的報道和評論,一度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刊發報道稱,“最近,有20來位中國教師,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錯誤,掀起了一場風暴”。
談起參與研究的動力,蔡朝陽和呂棟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孩子。他們的孩子目前都剛剛念小學。
“做這個專題之前一段時間,我正為一件事焦慮——就是兒子的上學問題。”呂棟告訴記者,“所以郭初陽提出研究小學語文時,我還是很感興趣的。至少可以借此好好看看兒子上小學到底將讀些什么玩意兒。”
蔡朝陽在綜合評估文章中寫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論,無法高屋建瓴從而頤指氣使。在考察全部3套教材時,我的底線在于:我是一個4歲孩子的父親。”
而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作家葉開也表示,他對小學語文教材的關心從女兒上小學開始。
“寫這些文章,我還跟我妻子商量過是否值得。我們交流后,她支持我這么做。小學語文不僅讓我們自己的女兒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葉開說。
該書的策劃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陽繼波告訴記者,雖然他兒子所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并不是上述3個版本的,但他在閱讀了這份研究報告后,再翻看兒子的課本時,發現也有類似的感受。
“我覺得現在小學生的閱讀環境和教材有些糟糕。”陽繼波說,“和我們上小學時所用的語文教材相比,現在的教材是有進步,但進步得比較慢。雖然達標了,但還不能算出色。”
